|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召开专家研讨会共话法律前沿问题 文 本刊记者 戴燕军 图 曹璐 随着“互联网+”概念的不断铺开,利用手机APP等网络平台运营的新型行业不断涌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涉及网约车、家政服务等各种服务型行业。7月28日,有关部门率先对网约车进行了规范,对外公布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一时间,各家公司纷纷作出回应。“滴滴出行”表示,《暂行办法》从国家法规层面首次明确了网约车的合法地位。“优步”表示,《暂行办法》的出台使我国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首个颁布此类全国性法规的国家。按照规定,各地应在11月1日《暂行办法》施行之前制定落地细则。但从目前看,各方观望氛围浓重,对一些焦点问题大多采取了颇为谨慎的态度。然而,在这些新型运营模式下,如何把握从业人员与网络运营主体之间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则成为司法实践亟待厘清的问题。 2016年8月26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召开了“‘互联网+’背景下劳动关系认定专家研讨会”,就“互联网+”经营模式下提供劳动力服务的用工类型和特点、单位与个人达成“不属于劳动关系”协议的性质以及在此情况下如何保护个人的合法权益、“互联网+”经营模式下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新型劳动争议案件呈高发态势司法裁判和认定存在诸多难点 “互联网+”这一概念是在2012年被首次提出,作为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被定位为提升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的重要手段,并于2015年被写入了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互联网+”经营模式对传统行业下劳动关系的用工模式形成了冲击和挑战,近期涉“互联网+”企业的劳动争议案件呈现了高发的态势。据不完全统计,朝阳法院从2015年1月至今,一共受理与互联网有关的劳动争议案件140件左右,极为典型的案件为118件,包括“河狸家”“蓝犀牛”“58到家”等案,虽然数量在该院收案比例上微不足道,但由于这些案件存在群体性强、试探性诉讼多,存在很多潜在的诉讼人群、争议焦点集中在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上等特点,因此在处理起来确有难度。 根据该院已经形成诉讼的涉“互联网+”经营模式劳动争议案来看,从业人员业务获取类型大致可以分为3类。第一类可称之为“指派业务型”,即消费者将消费信息输入网络运营平台或者网络运营平台收集消费信息后,将服务信息指派给特定的从业人员,该从业人员根据指派完成消费服务;第二类可称之为“共享业务型”,即消费者将消费信息输入网络运营平台或者网络运营平台收集消费信息后,将服务信息在从业人员终端中共享,由从业人员选择进行消费服务,或者由从业人员按照一定标准(如时间先后、距离远近等)进行竞争,由竞争优胜者完成消费服务;第三类可称之为混合型,即上述两种类型同时并行。从业人员既可以由网络运营平台指派提供服务,同时又可以通过共享消费信息自主选择提供服务。另外,从业人员的报酬获取也存在不同的类型。第一类为从业人员提供服务后,消费者将服务费用支付给经营平台,从业人员从经营平台获取报酬(按服务次数逐次收取报酬或者按一定周期结算报酬),消费者不向从业人员支付费用;第二类为消费者将费用直接支付给从业人员,从业人员在向经营平台支付部分费用后(或者在获取业务时向经营平台提前预付费用),将剩余费用留作自身报酬;第三类为消费者将费用直接支付给从业人员作为报酬,从业人员不向经营平台支付费用。 据该院从事此类案件审理的法官介绍,因为“互联网+”经营模式下的从业类型远远丰富于传统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导致司法裁判和认定出现诸多难点,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人格从属若即若离。“互联网+”经营模式下,从业人员确实需要从网络平台获取从业信息,接受业务信息的“安排”,但又不具有传统劳动关系下明显的人身依附特征,比如共享业务型的从业人员仅仅是持网络终端与网络平台建立联系,除此之外,双方之间没有其他隶属特征。第二,经济从属含混不清。从业人员完成相应业务后,从运营商处获得报酬,尤其是按照固定周期结算报酬的情况确实存在,但从业人员自行收取费用作为报酬,或者自行收取费用后将部分费用作为报酬的情况也大量存在。尽管前者与传统劳动关系的劳动报酬支付形式相比体现出更为明确的经济依附,但往往又是按照从业次数或业务量决定报酬金额,不存在固定的薪酬保障;而后者则基本没有明显的经济从属特征。第三,业务从属难以界定。从业人员确实从网络平台获取从业信息,但其所从事的业务是否属于网络平台运营商的经营业务较难界定。从运营商通过网络平台为从业人员提供业务信息的角度来看,从业人员从事的业务似乎应属运营商的业务,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运营商实际从事的是网络平台的建设运营,是对于业务供给信息的收集发布,并不直接经营实体业务,这又与业务从属性存在差距。第四,“不属于劳动关系”协议的效力认定难以权衡。现有的案件中已经出现了网络运营商与从业人员签订协议,明确约定双方不属于劳动关系的情况。基于民事活动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只要不存在双方意思表示不真实、不自由的证据,双方所签协议当然应属有效。但从劳动法社会保障理念的角度考虑,劳动关系是否成立应属法定范畴,不应由当事双方自由意志决定,且相对网络运营商来说,从业人员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故双方所签协议的效力认定存在难以兼顾的利益衡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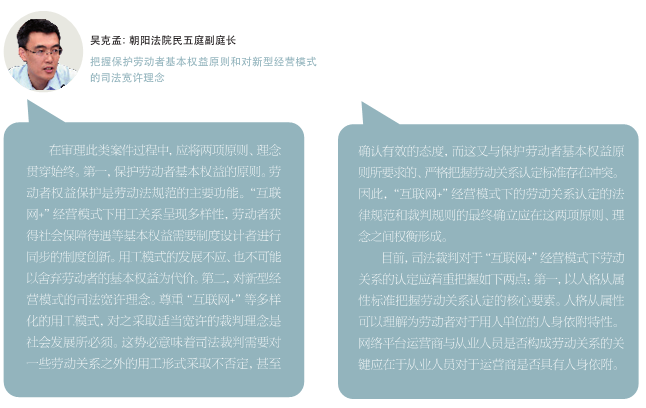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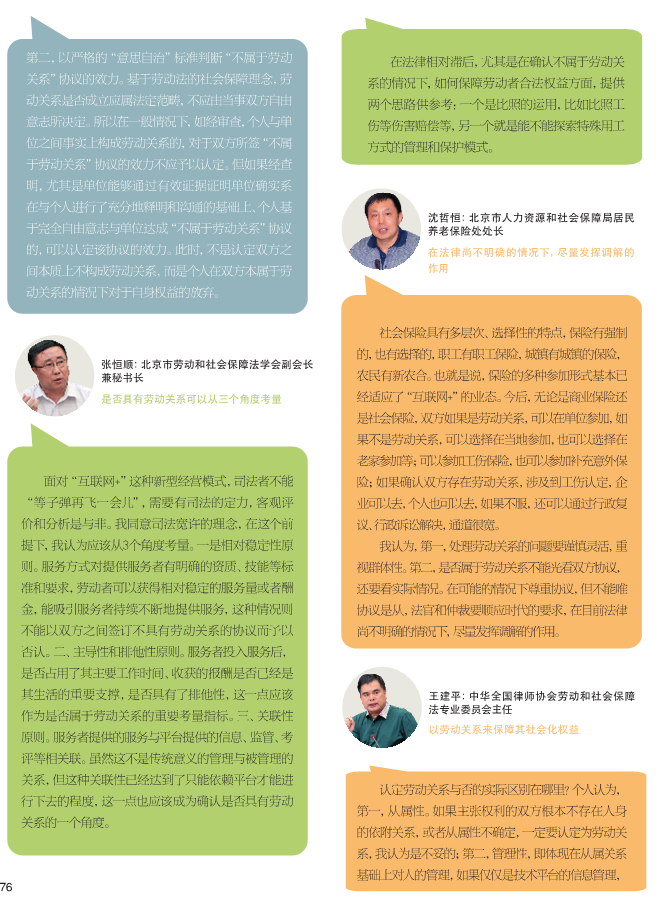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