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彭新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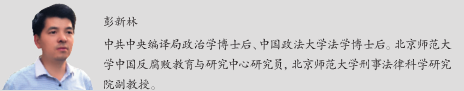
我国反腐境外追逃的现状 近年来,腐败分子潜逃境外的案件时有发生,成为我国腐败犯罪发展变化的一个新动向,也是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和刑事司法面临的一大难题。虽然腐败分子外逃的路径和情形多种多样,但大多是抱着“捞了就跑、跑了就了”的心态。据统计,腐败分子逃亡目的地主要集中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危害十分严重,我国司法机关肩负的境外追逃任务十分艰巨。加强反腐境外追逃工作,既是新形势下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客观需要,也是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犯罪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有利于消除腐败分子妄图逃避法律制裁的幻想,更好地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际声誉,增强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信心。 我国党和政府一贯高度重视反腐境外追逃工作,并取得了明显成效。2008年,中央印发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强纪检、审判、检察、公安、监察、审计等执纪执法机关的协作配合,完善跨区域协作办案及防逃、追逃、追赃机制,进一步形成惩治腐败的整体合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谈到要加强反腐败追逃追赃工作。这充分表明了我们党和政府坚决查处腐败、维护法纪权威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也为我们有效预防和惩治腐败犯罪分子外逃并追回犯罪资产指明了方向。迄今为止,我国政府已签署和参加了包括《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内的多项双边、多边国际公约,先后与57个国家缔结111项各类司法协助类条约,为开展境外追逃和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 我国反腐境外追逃工作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了引渡、遣返、劝返、异地刑事追诉和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等多种方式并存、相互补充、突出重点的境外追逃方式体系。从近年来反腐境外追逃的实践看,我国境外追逃工作确实取得了不少成绩,已成功地将一大批外逃的腐败分子缉捕归案,效果非常明显。但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反腐境外追逃工作尚存在一些问题,亟待研究解决。择其要者如下: 第一,境外追逃困难。由于各国政治制度、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法律体系上的差异,在我国反腐追逃的实践中,面临着条约前置主义、死刑不引渡、政治犯不引渡以及对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缺乏足够信任等问题,这使得大量的引渡或者遣返请求等被外国拖延、搁置甚至拒绝,这已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境外追逃的效果。 第二,境外追逃成本高昂。高昂的追逃成本也成为制约我国境外追逃工作的一大瓶颈。相比于国内追逃,境外追逃因涉及到公务往返、双方谈判、证人出庭、调查取证等众多程序,其追逃成本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 第三,境外追逃技术条件有待提高。长期以来,我国检察机关境外追逃之所以存在较大难度,境外追逃工作总体成效离党和人民群众的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应当说与检察机关运用技术侦查手段有限和技术装备不足是存在一定关系的。 第四,境外追逃经验还不丰富。虽然我国与外国缔结了大量涉及引渡、刑事司法协助等事项的条约,但司法机关引用这些国际条约的概率却很低。其中,重要的原因是我国一些地方的办案机关对境外的情况、法律制度等了解不够,追逃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均不高,表现出一定的畏难情绪,这给我国境外追逃工作造成了很大障碍。应当知道,境外追逃在很多时候斗的是智慧,拼的是意志,靠的是经验。 对改进我国反腐境外追逃工作的建言 为进一步改进新形势下我国对腐败分子的境外追逃工作,建议着力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加快做好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有关要求的衔接,破解境外追逃的法律障碍。一是要灵活处理死刑不引渡问题。在目前我国不太可能废除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死刑的情况下,建议采取灵活处理的方式,适时在双边引渡条约或者司法个案合作中,规定保证不判处被引渡人死刑或者作出不判处死刑的量刑承诺,从而以积极的姿态面对国际反腐追逃工作。二是要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等国内立法,使之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政治犯不引渡、双重犯罪原则、本国国民不引渡等问题上的规定和要求相衔接,从而为成功追捕外逃贪官,排除国际司法合作中的法律障碍创造条件。 第二,境外追逃与境外追赃双管齐下,发挥反腐追逃的整体合力。境外追逃和追赃都是开展国际反腐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密切关联、相辅相成。一方面,既要高度重视境外追逃工作,加大合作力度,提高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水平,把缉捕潜逃境外腐败分子作为对外司法合作的重点工作,综合运用引渡、遣返、劝返等方式,增强打击跨国、跨区域腐败犯罪的实效;另一方面,又要积极开展追缴和返还腐败资产的国际合作。通过追缴境外腐败犯罪资产,以此摧毁腐败分子在境外生存生活的物质基础,挤压其生存空间,截断腐败分子的退路,迫使腐败犯罪分子甘愿回国自首,或最终被强制遣送回国,以此实现以追赃促追逃的效果。 第三,实行关口前移,进一步健全防范腐败分子外逃的工作机制。与追逃、追赃相比,预防腐败分子潜逃,积极健全防范腐败分子外逃的工作机制更是一项治本之策。要强化防逃意识,增强防逃工作的主动性和预见性,依法果断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尽最大可能将腐败分子控制在境内。要统筹部署和推动腐败分子防逃工作,加强检察与纪检、公安、法院、海关、工商、审计和外交等部门的合作和信息沟通,完善相关制度,逐步建立起防逃网络。要完善官员配偶和子女移居海外、出国留学等事项的报告和备案制度,防止领导干部当“裸官”,坚决遏制腐败分子外逃现象的滋生蔓延。 第四,继续深化司法改革,树立司法公正形象。田晓萍副教授在《我国引渡外逃经济罪犯的法律障碍和对策—以赖昌星遣返为视角》一文中指出,西方社会对我国的司法公正往往存在偏见和疑虑,因此每当我国提出引渡或遣返请求时,根据我国国内法,本已是证据确凿的重大案犯,但被请求国仍会就被请求人是否受到公正的司法待遇问题展开一系列的评估等等。评估结果直接影响被请求人能否顺利引渡或遣返回国。可见,树立司法公正形象对于能否成功引渡或遣返外逃腐败分子十分重要。而要树立司法公正形象,增强外国对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信心和信任,就应当继续深化司法改革,严格规范司法行为,进一步优化司法权力配置,更好地尊重和保障人权,不断提高执法办案水平和司法公信力。 第五,加强检察机关境外追逃的技术力量。腐败分子境外追逃要有较先进的技术条件和装备作保障。要深入实施科技强检战略,大力加强检察机关境外追逃的技术力量,推进追逃技术装备的现代化,重点加强移动定位设备、电信监控设备、视听技术装备等高科技装备建设,探索对数据存储介质检验、录音录像资料识别、数据恢复固定、心理测试等技术侦查手段的探索使用,把增强检察机关境外追逃的技术力量作为提高反腐追逃成效的重要途径。 注: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腐败犯罪及其防治对策研究”(批准号:14CFX019)的阶段性成果
|